在網絡出現以前、旅行還是奢侈而困難的1928年,一位年輕的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 為西方世界帶來他們從未接觸和明白的異文化窗口 —- 《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這本書不但是史上首本為一般大眾而寫的人類學研究書藉,更是從薩摩亞這個遙遠的大洋小島,為西方一直困擾的青少年問題帶來亮光和新洞見。甚至五十幾年後,圍繞《薩摩亞人的成年》的學術爭論依然歷久彌新,引起學術界軒然大波。
【一個年輕女學者的遠行】
1922 年秋天,年輕的Mead 選修了被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的課程,Boas不僅嚴格且要求甚高,但作為那個時代的學者,他卻完全不介意跟女性合作,為Margaret造就莫大成長和發展的機會。
當時,西方社會中許多人主張某些種族先天就是高人一等,亦即為「優生學」,但Boas卻反對這種論述。他認為沒有種族是天生比較優秀,因此他視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從優生學家爭論人性的可塑性,讓大眾知道:人性的表達更多是來自於後天文化環境的塑造,而非被先天遺傳因素所限。Boas亦挑戰當時同年代的大多數人類學家並不和研究對象長期相處,而只是根據旅行者的描述來了解原始部落文化。他堅持人類學家應該多認識不同族群、理解他們的習俗、學習他們的語言,並且詳實紀錄觀察到的一切細節 —- 這樣的研究才可將人類學昇華為真正的科學。
就在這個背景,Boas起初希望Mead能研究美國原住民,但是她對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地區情有獨衷,就執意前往南太平洋;折衷之下,由美軍管轄的薩摩亞就成了Mead 首個長期實地研究的目的地。她的導師Boas 所給她的命題為:鑒於在西方文明國家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現象,那麼,在原始文明中這一現象是否同樣存在?
1925年,充滿期待的Mead 如此形容這次旅程:
「我擁有的膽量是出於幾乎全然的無知。我讀了所有關於太平洋群島民族的文獻……但我自己從未出國或搭過船,也從未說過外國語言或是單獨待在旅館裡。事實上,我一生從不曾獨自過上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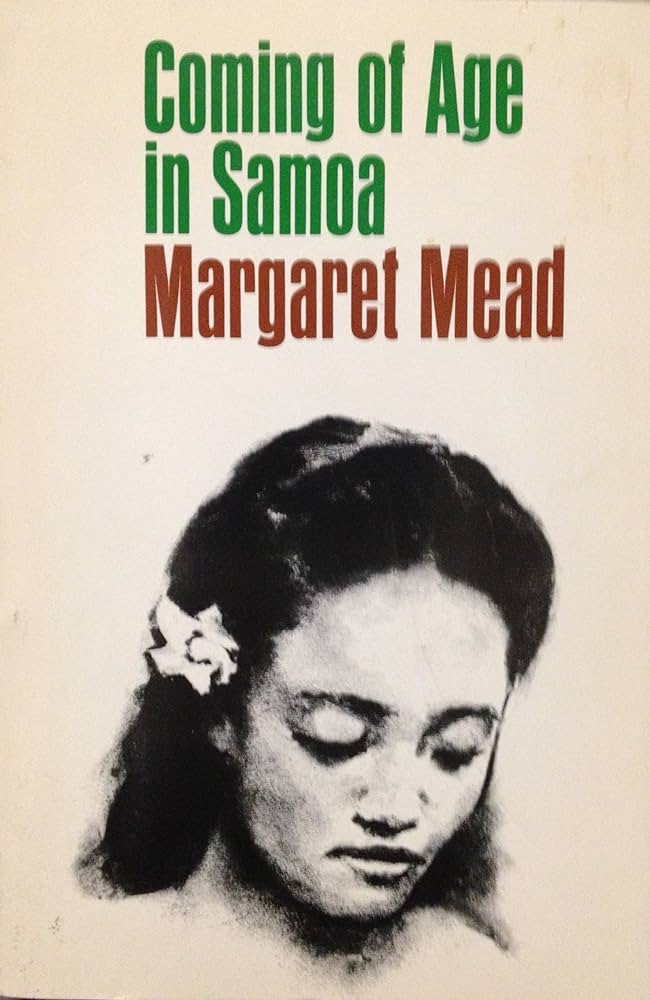

【薩摩亞的隨性與自由】
到達遙遠的薩摩亞後,Mead 將她的實地考察對象定為處於青春期的薩摩亞女孩。作為一名二十剛出頭的女性人類學者,她觀察到這些當地的青少年並沒有反映出廣泛社會對青春期男女的定型 — 本質上叛逆、行為與社會標準相互衝突、為成長壓力所困擾。相反,青春期對一眾薩摩亞青少年來說,那是一段無憂無慮的大好時光。
Mead 首先在書中記錄了薩摩亞人典型的一生:出生時沒有隱私,並舉辦盛大的宴會來慶祝;父母對孩子的管教雖然有懲罰,但大多是儀式性而不造成嚴重傷害;孩子從小就被期望參與有意義的工作,男孩接受釣魚教育,而女孩則更注重學習照顧兒童。他們有日常的雜務、只被賦予有限度的責任,也相對開放地看待性事。Mead 形容薩摩亞的生活相對單純、自成一套,不像在美國的青少年般有各種大小事需要煩心。
此外,薩摩亞人的日常生活以「戶」為單位,戶由數個互有關係的家庭所組成。因此,一個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有著多人照料,使他們對親生母親不會形成格外強烈的依戀關係。而如果一個孩子對與她住在一起的親戚不滿意,她可以輕易搬到同一戶的另一個家庭。因為如此的環境,薩摩亞人的生活中少有衝突和競爭,父母對孩子也少有強制性的管教。另外,薩摩亞人的童年大多都親眼見證家人的出生和死亡,人們沒有禁止兒童遠離這些情景的慣例。Mead 總結,正是得益於如此無拘無束的環境,造就了薩摩亞人淡泊隨和的性格,他們不會為感情問題而偏執痛苦,熟悉並懷抱生死,亦因此沒有精神困擾:「在薩摩亞這塊土地上,沒有人孤注一擲,沒有人願作大犧牲,沒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難,也沒有人為了某種特別目的而殊死拼搏」。
基於以上的觀察,Mead 因此主張伴隨青春期而來的種種張力和衝突並非生理使然,而是後天社會文化因素所形成。她指出由於西方文化對性、死亡和出生問題的禁忌,孩子們沒有一個自由的環境來表達自己,因此產生了攻擊性,甚至犯罪的態度。在教育面向,Mead 認為人們應該教導孩子如何思考,而非教導其該思考什麼,也建議父母不要將自身宗教信仰強加在子女身上。未成年人應該要知道更多開放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擁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道路。她試圖論證如此沒有限制表達的單純成長環境,原來能夠有效幫助青少年度過一個平靜的青春期階段,而薩摩亞人的生活就證實了這一點。
Mead 於1928 年將她的觀察和發現出版成書。她的措詞不但細膩生動,也沒有艱澀難懂的學術用語,讓薩摩亞的人文景色躍然紙上,因此成功吸引大眾目光並獲得廣大成功。更重要的是,這書為當時歐美學術界正在激烈爭論的兩種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証,Mead 藉著她的研究給予了明確立場:正是後天文化一手打造了複雜的人性。《成年》在往後數十年被譯為數十種語言,在各國的暢銷勢頭經久不衰,並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讀本。而Mead 因著她的研究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女人類學家,並被視為文化與人格思想學院的先鋒之一。
【學者間的挑釁和思辯】
時間來到1983 年,在Mead 去世之後,另一位人類學家Derek Freeman 出書反駁《成年》的論述,為學術界帶來震盪。Freeman剛開始研究時也是Mead 的粉絲,因此在四十年代他緊隨Mead的腳步,同樣在薩摩亞中進行實地研究。但他所觀察到的情景卻與Mead的描述大相徑庭,於是就寫成《一個神話的形成與破滅》,針對米德的結論逐條進行反駁。
Freeman 的調查結果並非片面之詞。他不但在薩摩亞居住許久,長期深入薩摩亞地區,亦成功被薩摩亞人所接納,與他們同吃同住,並且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他甚至在獲得當地人的充分信任後,還被准許參加重要的酋長會議,從而掌握大量一手資料。因此他的研究也是相當紮實,令人無法輕易忽略他的論點。Freeman認為,Mead 在當地調查時間僅為五個多月,對薩摩亞的語言知識不足,並只住在當地的美國人家庭。他又指出Mead 過度強調文化面而忽略了生物學面向,她對薩摩亞像田園詩般的描寫徹是一個誤導,薩摩亞並不如Mead書中所說那般美好和簡單。
然而Freeman 的書本身也存在爭議,並遭到人類學界的強烈反對和嚴厲批評。其中一位學者Eleanor Leacock 於1985 年前往薩摩亞,對城市地區的年輕人進行了研究,並反駁Freeman的說法有嚴重缺陷:Mead 著名的實地考察是在一個尚未殖民的外島上進行,但Freeman卻是在薩摩亞一個飽受藥物濫用、結構性失業和幫派暴力困擾的城市貧民窟進行了實地考察,如此的比較絕對不公。亦有其他學者認為,在Mead和Freeman兩者的研究之間經過了幾十年,薩摩亞的原始文化亦因基督教的融合而已被改變,因此Freeman的著作並沒有使Mead的研究失效。
【人類學的意義】
Mead的著作讓人類學進入社會大眾的眼界,而從此引起的各方討論亦讓人們更多思考和思辯人類學的意義和為我們世界所帶來的影響。人類學的誕生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為什麼世上還有另一種與自己不同的文化?唯有當兩個極為不同的種族相遇,人們才會開始發現和思考這樣的問題,而出於對於這些文化差異的好奇,十九、二十世紀人類學得以悄然崛起。
不得不注意的是,當時的人類學家大多都有美化原住民或原始文化的傾向。他們述說原始文明中不存在如文明社會中殘酷的戰爭現象;或原住民常常有著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他們視大自然為神靈,也就因此抑制了對資源過分貪婪的佔有欲。然而隨著人類學的發展和豐富,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些美化大多不能成立,或不能以簡單的二元化解釋原住民文化的實踐和價值觀。初期的人類學家可說是把原始文明當成一面鏡子,用以反襯他們身於的所謂文明社會的各種醜陋現象。而Mead在薩摩亞的研究更有其特定的背景,在二三十年代優生學說已達白熱化之時,她的實地考察是建立於要論證文化決定論勝於生物決定論的前設之下。
雖然如此,Mead的《成年》無可置疑地為人類學帶來關鍵而美麗的發現,她一生寫了許多書、發表數不清的文章,講過無數場演講,她的主張一直堅定不移,致力於改善世界:她反對過度干預原住民生活,或將原住民當作珍禽異獸;她不希望人類學家只會跑統計數字,而忽略原住民是同為人類、是我們在世界的同伴。
Mead本人亦改變了那個年代那的人們對女性的刻板想像,被視為女性主義的先驅。她擁抱自己的女性身份,同時也是一名母親,她有能力在學術界開疆拓土,做著非傳統的事情、宣揚非傳統的概念,並在傳統被男性把持的領域獲得認可和名聲。紐約客雜誌曾稱她是「人類學領域中最受廣泛讚譽的學者」,她將人類學從冷僻的研究領域帶進社會大眾的認知裡,也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別懷疑,少數有心的志士便能改變世界」。

參考資料: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623767/
https://www.nytimes.com/1983/01/31/books/new-samoa-book-challenges-margaret-mead-s-conclusions.html
